
程美东:品格与选择——早期中共北京党组织发展中的历史文化因素
编者按: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提出的要求,《北京大学校报》特开设旨在探讨北京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的栏目——红色北大。本期特邀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程美东撰文阐述中共北京党组织的历史发展与选择,以纪念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所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北大人。
北京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成立的两个组织之一,早期北京党组织(1921—1927)的成员很多都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同时他们很多人为党的事业发展呕心沥血、作出过重要贡献 。但是在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舞台上,却少见早期北京党组织的成员的身影,其原因何在?本文将就此展开一些分析和研究。
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的历史命运
目前学术界能够确定的1920年北京党组织成员至少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范鸿劼、缪伯英、何孟雄、张申府、张太雷、李梅羹、吴汝铭、宋介(汉奸)、陈德荣、江浩等17人。这17人中,牺牲的烈士和病逝的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工作中病逝)、范鸿劼、缪伯英、何孟雄、张太雷、江浩(病逝)、李梅羹(病逝),开除出党的有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吴汝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能够确定的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员至少有12人,他们是:“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开除出党)、刘仁静(托派)、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叛徒)、张太雷”,牺牲和病逝的7人。
中共一大后成立了北京地委,由李大钊担任书记,罗章龙、高君宇、李梅羹为北京地委委员。1922年,产生范鸿劼担任委员长包括张昆弟、包惠僧、何孟雄、安体诚四位委员(这届委员大革命前后全部牺牲)的北京地委。
1923年6月北京区和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何孟雄担任委员长,张昆弟、范鸿劼、张国焘担任委员。1924年3月北京区委和地委改组,李大钊担任委员长,蔡和森、张昆弟、何孟雄、范鸿劼担任委员。1924年秋北京区委和北京地方地委改组,赵世炎担任委员长,范鸿劼、高君宇、陈为人(病逝)、彭桂生、李国喧等担任委员。1925年春,陈乔年担任书记,赵世炎、范鸿劼、陈为人、彭桂生(托派)、李国喧担任委员。1925年9月新的北京地委成立,赵世炎担任书记,陈为人、李国喧、陈毅为委员。1926年1月刘伯庄(托派)任北京地委书记,陈为人、卓恺泽(牺牲)、李渤海(叛徒)担任委员。
以上北京地委和北京区委在大革命时期主要领导多数人牺牲或者病逝在工作岗位。可以说早期北京党组织领导人信念坚定,不怕牺牲,无愧于大钊先生开创和孕育出来的党的最早发源地的名号。虽然也有叛徒和脱党分子出现,但是这不是主流,是个别现象。总体上,北京地区党组织成员在大革命时期党中央担任重要职务的的高层领导很多,但是此后越来越少,这个可以从中共七大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委员会成员情况得到一定的说明。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
中央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洛甫)、蔡畅(女)、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陈绍禹(王明)、秦邦宪。
中共七大产生的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一位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北京党组织。44名中央委员中只有一位(陈毅) 是大革命时期北京地方组织成员。
综合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的历史命运就是:成为烈士的很多,展现出伟大的牺牲精神 ;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在大革命之后中国革命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的很少。这两点可以说是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的总体历史命运之特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主要原因当然主要是该组织众多在建党初期担负党内重要工作领导人的同志在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被反动派绞杀而过早地牺牲了。
北大师生风格气质与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政治品格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区组织领导人很多出身于北大,“一大”前的中共北京支部的成员共12人中11人是北大师生,只有一位缪伯英是北京女师毕业生,但是她当时就是北大出身的何孟雄的夫人,最早从北大人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所以,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总体上深受北大风格的影响,刻上了浓郁鲜明的北大人的色彩,他们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理论水平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李大钊是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一批理论家、革命家,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等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方面也都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撰写了很多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北京大学又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资料汇集比较多、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才比较集中的地方 ,所以北京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尤其在建党初期可以说其整体的理论水平在全国党组织中居于前列。1920年11月,他们创办面向工人群体的《劳动音》刊物,成为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机关刊物。1921年党成立前夕,他们又创办了面向工人大众的《工人周刊》,报道国际国内工人受压迫的情况,鼓励工人起来反抗压迫、改善经济状况、举行罢工斗争。1924年北京地委创办《政治生活》,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扩大马列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

《劳动音》杂志
理想高、情怀深、革命自觉性强。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基本都是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员,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选择是长期思考、自觉学习、理性选择的结果,不是出于维持生计的需要、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从追求真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角度来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所以,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用社会主义道路来改造中国怀有崇高的理想和深厚的情怀,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上的艰难险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革命的自觉性强。正是奠基于这个基础,所以北京党组织早期领导人总体上革命斗志旺盛、态度坚决、视死如归。
对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高度重视和践行。北大人理想主义浓厚,认准真理之后绝不妥协,在思想认识没有搞清之前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方向,这是北大人的执着和信仰决定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对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高度重视、格外重视,有的时候超过了对于特定环境下组织路线的重视。罗章龙、何孟雄是早期全国党组织更是北京市党组织的重要人物,1931年他们之所以反对米夫一手包办扶持王明上台的四中全会就是认为它不合法、不合程序,罗章龙在组织结论上中央认为其是“分裂中央”,何孟雄被中央认定为烈士。虽然我们党一直强调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一致,而且北京早期党组织也一直是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来要求党员的,早期北京党组织也是严格执行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组织路线的,但是当实际工作中出现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认识上、执行上的差距时,长期浸染的政治文化会对他们中个别人的政治实践产生偏向于思想路线的特点。这也可以说是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总体理想性政治品格的反映。当然我们不能过分渲染这种色彩,只是从微观的角度增加我们思考问题的深度而已。
早期北京党组织工作环境与党员的历史命运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很多重要成员长期在北京地区工作,像李大钊、范鸿劼、高君宇、陈为人等高级干部长期在北京地区工作,为何他们愿意、能够长期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从根本上当然是组织的安排、工作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需要。但是从微观上看与早期北京党组织的和谐、民主、融洽的工作环境有关。凭什么说北京早期党组织和谐、民主、融洽?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北京早期地方党组织没有发生重要成员退党、脱党、出大乱子的,而有的党组织就先后出现李达、李汉俊这样重要成员负气出走、脱党的事情。这种状况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与主要领导人的工作风格有关,李达和李汉俊脱党主要就是对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不满,而北京地区长期领导核心尤其是精神领导核心是李大钊。李大钊不像陈独秀个人英雄主义似的性格张扬,他谦虚、民主、老练、厚道、沉静的处事风格给早期北京党组织团结、融洽工作氛围的营造提供了很好榜样。早期北京党组织出身的党员中有退党的、有消极的、也有叛徒,但是重要成员中真正的叛徒主要就是张国焘。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总体是中国共产党员纪律严明、信仰坚定的反映,但与李大钊精神风范形成的氛围不无关系。李大钊虽然不是北方局的区委书记,但是他是北方局党的精神导师,他的正直正气和对共产主义的执着信念,总体上来说影响了整个北方区委、北京地区的领导人的政治风格。他的工作作风、人格品质对整个北方党组织领导人发生积极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李大钊先生工作的特色就是尽量宽容宽厚地团结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人士,尤其在国共合作之后,他在北京地区、整个北方是国共合作的领导核心,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可以说,为了统战的需要,李大钊组织了整个黄河以北的党组织,他能打开这种局面与他这种宽厚、团结社会上至军阀下至普通师生是有关系的。这种情况下北京党组织所承担的责任使命更大,北京地区的干部想要出去的可能性更小。而且已经习惯于跟大钊一起工作的人,也折服和心悦于这样的工作环境。而长期呆在北京地区,干部就缺乏了在不同岗位上展示自己才干的机会,他们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发挥更多、更大作用的空间就明显减小了。
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在后来党内职位不显著与当时北京地区党员的主体成分结构也有一定关系。北京地区的党组织是在李大钊先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由于他本人的职业因素,当时党组织内受到重用的人多数是国内大学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之后,革命干部的主体变为工农干部和莫斯科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原来国内的这些高校知识分子都退为次要的了,所占党内干部的比例越来越少。所以这些人的干部路线问题发生了变化,这时期在北方局与大钊一起工作的人肯定也会受影响。
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在后来党内职位不显著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人的信念和宗旨——实现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闹革命不是当官发财,不是光宗耀祖,而是要消灭不平等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在这样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的驱使下,他们只以党的利益为重,把革命工作分工的不同视为革命事业的需要,根本没有把职务高低、权力大小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想着如何齐心协力实现人民解放、国家解放、民族解放、人类解放。所以,大革命时期一个人党内职务的变动非常频繁,这一届是中央局成员、中央委员,下一届可能什么都不担任,但是一点没有减少他们革命的动力。
南方革命中心的不断强化对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的影响
北京大学是北京党组织的发源地,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中心工作就在南方,这个格局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决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北京是北洋军阀政府所在地,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反动势力太强大,他们公开以残暴的手段来剿灭共产党的组织和一切活动,而南方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相对宽松一些,革命依靠力量更强大一些。中共一大在上海和南湖召开,国共合作后工作中心转移到了广州,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一大至五大分别在上海、广州、武汉召开,没有一次大会在北方召开,这个事实就生动地说明了南方对于革命的重要性。
大革命失败后,从1927—1934年,这八年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中心是湘鄂赣闽粤豫皖川等南方红色根据地,在这些地方上演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大剧,使得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南方红透了半边天。虽然在这个时候,北方也爆发过土地革命起义,也形成了一些根据地,但是无论是从时间的持久还是空间的广大以及动员人数的众多而言,北方的苏维埃革命之火远远没有形成燎原之势。
革命中心在哪儿,哪里的革命成员的创造性、奉献程度、历史功绩就要大,这种客观的革命环境使得主要活动在北京为核心的北方地区的共产党员们大展身手、建功立业的机会和舞台就要小得多了。
从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的党员干部的命运审视北京党组织成员的历史命运
我们在今天评价、认识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的历史命运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北京地区党组织体系的党员情况,应当要扩大到整个北方区委领导的党员干部的历史命运。因为在很长时间内,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方委员是重叠、半重叠的组织系统,领导成员不少是同一拨人担任。
1923年7月,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北京区执委兼地执委)成立,何孟雄、李大钊先后任委员长。北京区执委负责北京、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山西、吉林、黑龙江、辽宁以及河南、陕西、甘肃部分地区党的工作。1925年10月—1927年5月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由李大钊担任,秘书:彭桂生、杨景山、陈乔年、赵世炎、范鸿劼、刘清扬、夏之栩、张兆丰、李怀才、罗亦农都担任过委员。通过这个名单我们可以发现,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的领导干部很多是重合的。所以我们在审视北京地区早期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时一定要和北方区委的党员放在一起,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
从这样混为一体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北京地区党组织成员的政治生命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其时空得到了空前的扩展。河南省委在大革命时期直接受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领导,王若飞就是当时河南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东北三省党组织也是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赵尚志等后来成为抗联领导的党员都是在北京区委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陕北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是李大钊和北方区委一手指导发展起来的。李子洲1923年春天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夏天受李大钊派遣到渭北、榆林、绥德等地开展党组织建设,1925年他在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陕北党团组织的基地。谢子长、刘志丹、马明方、郭洪涛、阎红颜等著名的革命家都是在这个党的基地的辐射影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北方区委为革命中心从南方苏维埃转到陕甘宁提前准备了火种,陕甘宁根据地党员的历史命运就是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的扩展和升华。
从这个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融为一体的事实上来看,整个东北、华北、西北,还有河南甚至江苏的一些地方党员他们的历史命运也都可以算是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的的组成部分。北京早期党组织给我们党奉献了很多英勇善战、慷慨赴死的烈士,也给后来的革命培养了许多功勋卓著、声名赫赫的重要人才!
(作者程美东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572期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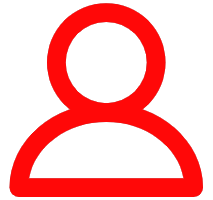


我要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全部评论 ( 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