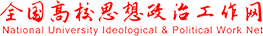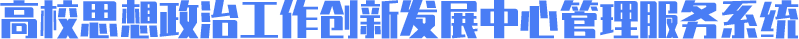一、案例简介
小黄自入学以来始终学业不振,对思政教师的劝导消极应付。在大一下学期收到第一次退学警告,在大二下学期收到第二次退学警告,依校规应予退学或试读处理。
在与小黄及其父母的沟通过程中,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小黄的父母积极地争取试读机会,代儿子做了试读期间的承诺和计划;而小黄自己非常消极,即使对是否想继续读书的问题也保持沉默。此外,小黄父母多次在旁人在场时打骂孩子,思政教师在谈话结束后还要追出门去阻拦他们的扇巴掌、踢踹等家暴行为。小黄的姑姑也数次陪同小黄父母来校,不仅会参与对小黄的吼骂管教,在小黄父母动手时也完全不阻止。
二、案例分析
(一)问题分析
为了和小黄取得有效沟通,我回避了小黄的父母,单独采用多种方法与小黄交流。终于在一次散步中,小黄放下心防,渐渐地开口说话了。小黄的家长对其教育颇为严厉,小黄既敬畏在家里家外都极具威严的父母和长辈,又对他们的要求多有抵触。在成长过程中,小黄逐渐形成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处世哲学”,既不敢对外在环境表现出任何正面对抗,潜意识中又从不愿遂家长的意。只要是父母要求他做的,他一定会做,并且一定是敷衍应付,通过达成一种消极结果以在和父母的“博弈”中取得某种形式上的胜利。值得说明的是,小黄并不能完全察觉自己的这种复杂情绪,他的认识处于“我就是不乐意做”阶段。
小黄的心理问题主要源自家庭的长期影响,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特殊性。
在思政工作中,我发现学生的自我认知和性格与其原生家庭有着密切关联,例如在父母不和、离异的家庭中成长的学生,可能性格乖僻、不善与人相处;经常遭到家人情感忽视或家暴虐待的学生,可能自暴自弃、对环境产生应激反应,等等。小黄在父母和其他长辈严厉而粗暴的管教下成长,至少在表面上对父母是完全服从、俯首帖耳的,性格上也是典型内向、寡言少语的表现。
小黄情况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其内在人格并未在父母的高压管制下自我否定、全盘接受父母的价值观,从而与家庭教育产生了较大冲突。父母的以身垂范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在强势的家庭环境中,小黄对这部分内容的否定不能够正常表达,甚至不能呈现在其表意识中,反而在潜意识中错误地泛化成了对父母的完全否定。最终小黄对父母的态度形成了表面完全服从、实质完全对抗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畸态。
小黄自述的一个生活场景可以很好地表征他的行为逻辑:在宴席上父母要求他给长辈敬酒,他不想做却又不得不做,于是他悄悄地违反父母教授的“礼仪”,把杯口抬高,或不喝尽酒,以示不满。小黄并未察觉到这是与父母的对抗,他只单纯地觉得自己喜欢这么做。
这种下意识的不合作,对小黄最大的伤害在于他将自己的学业也当作了对抗的手段。父母对小黄学业上的要求是优先级最高且最明确的,于是小黄报之以当然的消极态度,放任自己的惰性和玩心,从未考虑过自律自省。因为学校辅导员和家长保持沟通协作、共同督促其学业,我的形象在小黄看来类似于父母的代言人。在我的监督下,小黄能够勉强做到上课出勤、完成作业,并制订学习计划,但执行率极差。这种表面功夫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与父母对抗的延伸。
(二)对策分析
与多数原生家庭影响下的心理问题相似,对小黄的帮助应建立在对其错误认知的纠正上。在与小黄的谈话中,我帮助他重新探究自己逃避学习的原因,了解自己的潜在想法,探索引发自身负面情绪的潜在信念,直到他发觉自己追求与父母对抗的潜意识。
但是,小黄对父母观念的否定只是双方认知上的差异,不能简单地要求他与原生家庭取得全面和解从而解决问题。我主要通过积极肯定小黄的良性观点,为他提供抒发意见的渠道(主要是与辅导员及心理咨询师谈心谈话),使其对父母及长辈的部分否定能够适度表达,避免在学业上发泄自己的压抑情绪。此外,我要求小黄的父母杜绝家暴行为,并减少对小黄不适宜的强迫“教化”。
三、教育过程
(一)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在与小黄的父母接触后,我察觉到他们的亲子矛盾一部分正源于家长长期的自满和固执,对问题的症结完全不自知,将孩子的问题粗暴地归因于“贪玩,不学好”。我与小黄在此之后多次沟通交流,在谈话过程中注重表现出平等、尊重的态度,话题经常围绕各自的家庭和父母展开,终于在琐细的家常话里逐步挖掘出小黄的内心世界。
(二)解决问题
心理干预和辅导的对象不仅是小黄,也包括小黄的父母。初步了解了情况后,我并未急于规劝、纠正学生,而是与小黄父母进行了一次深度的交流,验证了小黄关于父母的一些说法,确定这些内容不是其在负面情绪引导下得出的错误认知。这之后我才继续与小黄的谈话,帮助他更加明晰地认识到自己“非暴力不合作”的行为逻辑,亦即他“不乐意”经营好学业的最关键原因。回顾收到第二次退学警告后的心境,小黄发现自己几乎没有绝望、崩溃之类的感受,相反内心深处是有快意的,也因此在这之后不是很愿意申请试读,情愿退学了之。
我对小黄的一些想法表示理解,并和他约定做他倾诉的对象。引导小黄将学业与对父母的负面看法之间的相关性“斩断”,重构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目标,将学业上的进步作为自我实现的重要手段。小黄于是主动写下了试读申请书。
对于小黄的父母,我明确地提出必须杜绝家暴行为,并配合小黄委婉地表达了他的看法。
此后,小黄的学业逐渐步入正轨,在大三整个学年每周都向我总结汇报。由于落下的课程比较多,大四后小黄延毕了一年,最终完成所有培养计划,顺利毕业。
四、总结反思
在这个案例中,小黄在成长的过程中,既未完全屈服于父母的高压管制而自我否定、全盘接受长辈的观点,又无法在强势的家庭环境中正常表达对父母一些想法的否定,最终在潜意识中错误地泛化成了对父母的完全否定,形成了表面完全服从、实质完全对抗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畸态,从而严重影响了学业。
该案例有一定特殊性,但对于大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和辅导有一些普遍规律可参考,主要在于以下几个环节。
(1)在快节奏、多线程的工作中,要保持细腻、敏感的同理心,有放下手头工作、沉下心谈心谈话的责任感。
在本案例中,如果我没有体察小黄异常的消极态度、细究其原因,仅在其父母的推动下就为他办理试读手续,可以预料,没有解开心结的小黄还是难以继续学业,最终只是多浪费一些时间。
(2)通过有技巧的沟通交流,与学生达成彼此信任的关系,从而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内心想法。
在谈心谈话的过程中,要尊重学生,设身处地地理解学生的心情,积极地关注学生,不吝赞美和肯定。注意以正面的肢体语言传达正面的信息,坐姿表现出平等和兴趣,保持自然和持久的目光接触,增强学生的信任和安全感,激发其倾诉的勇气,给其以积极暗示。此外,还要注意不提不适当的问题,认真倾听、耐心鼓励,以重复语句激励学生继续讲。为了引导学生陈述父母相关的内容,我分享了自己的情感体验,使学生产生亲和感,从而更愿意开放自己。
(3)对于学生的认知表现,要谨慎、正确识别其中的真实部分、扭曲部分和错误部分。
如果对于学生没有正确的认知,则后续的心理干预和辅导就建立在错误基础上,不仅难以取得效果,甚至会有负面影响。在该案例中,初步了解了小黄对父母的负面看法后,我并未急于规劝、纠正学生,而是与小黄父母进行了一次深度的交流,验证了小黄关于父母的一些说法,确定这些内容不是其在负面情绪引导下的错误认知,之后才继续与小黄谈话,帮助他更加明晰地认识到自己“非暴力不合作”的行为逻辑,亦即他“不乐意”经营好学业的关键原因。如果小黄对父母的负面情绪来自他的错误认知,那么此时不加以验证和辨别、急于开展心理干预,无异于火上浇油。
心理辅导的过程不局限在当下心理问题的解决,后续伴生的学生心理、生理各方面状态的改变等过程,也需要足够的重视。在本案例中,小黄辨明自己对父母的错误态度后,是重新建立目标和信仰的关键阶段,不可在此时放松警惕、掉以轻心,应当给予学生充分的关心和引导,确保他能够顺利度过过渡期。如果在这个阶段没有新的行为逻辑填补内心空白,学生可能丧失目标、失去追求,乃至陷入新的心理危机。
案例作者:刘张鹏,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