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简介】冯雪平,女,汉族,1999年9月生,河南项城人,现就读于广西民族大学2018级汉语言文学01班(写作方向),文学院本科学生第一党支部预备党员。曾获广西首届创意写作大赛“诗歌一等奖”及“微型小说一等奖”,第三届相思湖诗歌大赛一等奖,广西高校图书馆“学问杯”影评大赛“优秀奖”;曾在《广西文学》发表微型小说《囚禁》(获《微型小说选刊》转载),《我们与爱的距离》;在《广西民族大学报》、校公众号发表诗歌、微小说;《右江日报》发表散文。
自豫至桂——在民族怀抱里诗意地栖居
(一)故乡与他乡
《尚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豫州位居九州之中,而今河南省大部分属豫州,故简称为“豫”。河南项城,就是我的故乡。项城在周初年为项子国,久经历史风霜,有南顿故城,袁世凯故居等多处文化遗产。这里典藏着千年的文化遗墨,氤氲着馥郁的芝兰香气。生于斯,长于斯,是我的福气。爱上文学,也许是源于河南人血液里跳动的文化基因。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姥爷王学东是我的启蒙老师。在那个贫瘠的年代,村里的教师屈指可数,他就是其中之一。姥爷总是笑吟吟的,他的达观心态与真诚的人生态度使我终生受益。记得三年级时,我第一次学写作文,对着空白的方格纸一筹莫展:我为什么要写?要写什么?能写什么?对那时候的我而言,写作的世界犹如一个陌生的国度。而姥爷出现了,他循循善诱,一番话让我至今难忘:“写作是最简单的一件事,就像说话那么自然。你是能写好的,我看得出来。”
于是,我就这么自然地写下去了。写心声,写对外出务工的父母的思念,写回忆,写四月的麦田,我牵着风筝一头栽进地里。小学五年级时,父母决定在广西工作并定居,我随他们从中原远赴西南,过早品咂着身在他乡的漂泊感和疏离感,像一棵被嫁接到南方的乔木。
(二)此心安处是吾乡
1700.6公里,从百色到项城,这条路线跨越的不仅是我的童年,也是我的写作流域。转学后,我开始展现出不一样的文学敏感,浪漫而丰富的文学幻想,大量的阅读和写作,成了我用以对抗青春裂变和漂浮生活的解药。可贵的是,百色这座红城给予了我浓厚的革命精神熏陶与民族文化滋养,清风楼、红礼堂、百色起义纪念碑,是我成长的坐标,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在《右江日报》发表处女座《那时的花开》,是我走上文学之路的一个初始动力。
升入中学后,繁重的课业使我无暇他顾,文学被我藏在一个小角落,那里是小众而不为人所看重的世界。但作文课上,听着老师念诵我的文字,心里的火种还是隐隐地焕发着光亮。填报志愿时,我在每一栏专业方向上都写了“汉语言文学”。进入广西民族大学后,我逐渐明白:西南,中原,黄河,邕江,汉族,壮族……这些符号都成为我的人生路牌,但是无论在哪,文学就是令我我心安的方向。
(三)诗歌:我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在民大,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重新认识了自己。相思湖畔诗意的氛围,文学院良师益友的教诲陪伴,广阔自由的学术资源,党支部的悉心培育都为我的文学之路打下基础。大一时,唐谊军老师教授的“写作课”影响了我今后四年的创作。他幽默而亲切,向我们系统介绍了创意写作理论,用大量的写作任务锻炼了我们的文笔。在他的鼓励下,我的第一篇微型小说《糊涂鬼》成型了。
此后,在相思湖文学社里,我认识了一批优秀的学长学姐,他们爱诗歌,爱文学,爱浪漫,在交流中我不断成长,就这样,我找到了写作的快乐。大三时,我获得广西首届创意写作大赛的“微型小说一等奖”和“诗歌一等奖”,去玉林师范学院参加颁奖典礼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优秀的诗人与学者——李富庭学长,并在他和班主任吴先源的鼓励下,持续创作。此后,在《广西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微型小说《囚禁》。


这次旅程不仅让我真正走近了文学圈,也为我坚持写作提供了保证。后来,进入文学院本科第一党支部这个大家庭,我在党的怀抱里温暖生长。丰厚的民族文化氛围和特色的写作品牌为我的创作撑开一张网,让我走得更远,更久……。
2021年,得知我的组诗《接近天空的树》获得第三届相思湖诗歌大赛“一等奖”时,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诗歌,它一直是我疲惫人生的英雄梦想,那些晦暗的人生时刻都因为有了诗意的书写,变得珍重,独特。这是自豫至桂,奇妙的汉壮文化融合赋予我的文化滋养,使我在迥异的南北两地气候里,用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生活,就这样,我逐渐成长为一棵诗意地栖居在民族怀抱里的树木。
(四)小说——我绝对自由的梦游乐园
如果说诗歌是我的梦想,那么小说就是我向往的梦幻,我的精神殿堂,我的——“塔西提岛的月亮”。大学期间,我对东西方文学都十分着迷。我读毛姆,海明威和加缪,也读鲁迅,白先勇和石黑一雄。一句“人们在仰望月亮时,常常忘了脚下的六便士。”让《月亮与六便士》成为无数人的白月光。而小说,就是我心中塔希提岛的那弯月亮。
因为对悬疑冷静,残酷深刻的叙述陷阱的着迷,我创作出《囚禁》——被囚者与孩子的出逃经过,因为受到话剧《晚安吧,妈妈》的启发,我看到一对母女亲密而不相知的隔阂,创作出《我们与爱的距离》——描画出人们身上的“线”。看着这些幻想变成铅字,是我最自由也最快乐的人生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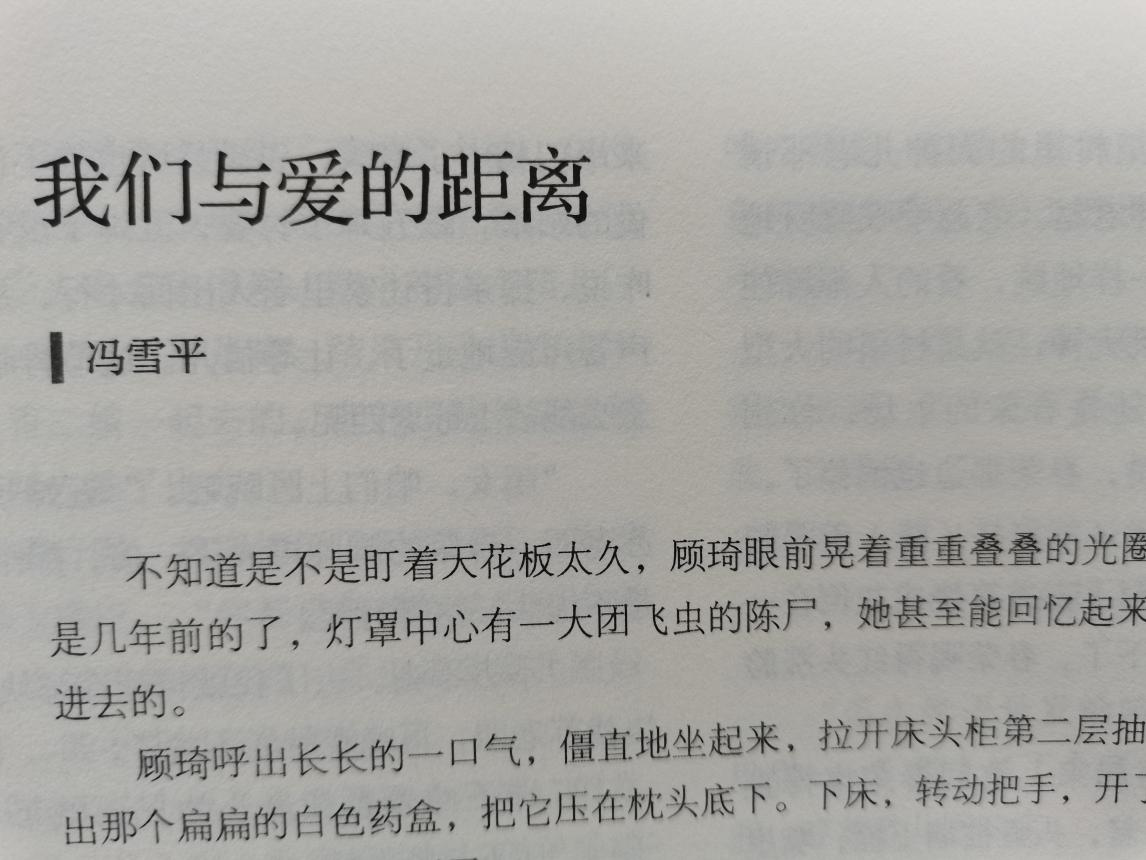
(五)爱文学,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有人纠结于文学的功利与非功利之争,有人扎根在故乡上书写本能冲动,而我的文学身份属实有些尴尬。在一次聚餐中,一位玉林的学者向我谈起对河南人印象如何不好,原因是河南骗子很多。我报以沉默,没有接过话,亦无一个字的应答,旁边的人连忙替我解围。这么多年,类似的问题一再出现,我被当做一个局外人反复审视。
仿佛人的刻板印象还和黄河的堤坝一样,壁垒分明。但我无法陈述游移在南北文化中,我无法彻底拥抱其中一种的尴尬。也无法接受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文化的指责。我看着他们彼此妄自揣测,看着他们误解,轻视对方的生存方式,十分心酸。即使今天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消一天车程,但我们仍然隔着万水千山,去想象另一个自己。
南方永远找不到北方,北方到不了南方。我们彼此给对方定义,以此确定自己的方向。但始终,在我十几年的体认里,我知道自己还是一个北方人。因为,根扎在那里。我的过早被移植的命运也许改变了人生的花期和形状,但是北方一直是我的原乡,亦是回不去的远方。我固执地想念他,像想念南方飘不来的大雪,像想念我年迈的姥爷,我的文字里,永远都有一座城市,一条北方大街,一座平原。那是我文学生命的原型,也是我在南方遥望的方向。

在河南,我成了半个广西人,在广西,我仍然是个河南人。而在哪里,我才是自己呢?身份的模糊让我缺乏依托感。但在这些年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我终于明白,在五十六个民族里,一个“和”字就可以把我们全部系牢。我们身上的文化特质只有在共同书写时才显得精彩而生动。于是,我不再在文字中避开对两种文化的思考与批判,时常转换身份,坦然地抒发对于南方与北方的感情。因为我知道,无论哪一种语言,都在为脚下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蓝天书写。
怀着这些经验和感动,我将在民族文化的怀抱里诗意地描绘,在党的领导下,继续用最真挚而虔诚的笔触,最敏感而丰富的视角去挖掘广西——这块民族热土上的动人故事,书写关于人民大众的精彩诗篇,继续着我的文学道路,凝视着属于我的那抹皎洁。也许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种浪漫。但对我来说,爱文学,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因为热爱,所以深刻。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我要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全部评论 ( 条)